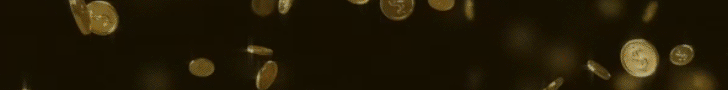范德比尔特移植中心是目前世界上最繁忙的心脏移植中心。 这是为中心今天的成就奠定基础的故事——讲述了这个首创的多学科、多器官移植中心成立以来 34 年的最初十年。 范德比尔特大学已进行了超过 12,300 例成人和儿童移植手术。 范德比尔特大学不仅每年进行的心脏移植手术比任何其他中心都多,而且它还是三十多年前接受肺移植手术存活时间最长的患者的地方。
作者于1992年手持移植人类心脏。
医学博士比尔·弗里斯特
它始于一个电话。
1985 年,我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移植外科的研究员,在 Norman Shumway 博士的指导下进行手术。 Shumway 被认为是“心脏移植之父”,这个称号适合我的导师,他是一位以研究为基础的科学家兼外科医生。 在我到达斯坦福大学之前的二十多年里,Shumway 系统地进行了基础科学和临床前移植研究,最终于 6 年 1968 月 XNUMX 日在美国进行了第一例人类心脏移植手术(Christiaan Barnard 博士,使用Shumway 几十年来发展起来的技术和知识,一个月前在南非进行了第一例人对人的心脏移植手术。)
一天深夜,我的电话响了。 电话的另一端是范德比尔特大学心脏外科主任哈维·本德 (Harvey Bender) 博士:“比尔,”他说,“艾克·罗宾逊 (当时的范德比尔特大学副校长) 和我希望你回到纳什维尔的家乡加入Walter (Merrill, MD) 开始并建立心脏移植计划。”
当时,心脏移植还处于起步阶段。 Shumway 以二十多年艰苦的基础和临床前研究为坚实基础,取得了有希望的早期临床结果,这表明心脏移植有一天会成为常规。 然而,在那一刻,田纳西州还没有进行过任何一次心脏移植手术。 该领域仍被认为是实验性的。
我对 Bender 的提议很感兴趣,但我设想了一个比他提议的更宏伟的梦想。 那个梦想是创造一个新概念——一个屋檐下的多器官和多学科移植中心。 没有人做过。 宏伟的愿景将包括更全面、以患者为中心的移植护理——不仅适用于心脏,也适用于多种器官。 这样的规模将带来更好的患者护理和其他项目永远无法实现的协同作用。
Bender 的电话激励我进一步研究和完善我脑海中一直在思考的东西。 这是一个大胆的目标,但我知道在正确的地方,有了正确的资源,并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不断进行的科学发现,它就会成为现实。
作者在 1991 年用一颗健康的 53 岁心脏替换了一颗患病的 18 岁心脏 …[+]
John Howser,范德比尔特医学中心
将斯坦福单器官模型扩展到多器官中心:协作
在斯坦福大学,Shumway 博士专注于打破孤岛。 他拥护协作团队的力量,明确尊重护士的重要角色(对于那些早期的心脏外科医生来说非常不寻常!)和移植团队的所有成员。 在他 1980 世纪 XNUMX 年代初期的指导下,他教会了我组织来自不同背景的专业人士组成紧密团队的力量。 他实践过,最好的移植护理是通过将研究、临床护理和教育专业人员聚集在一起来实现的。 我知道这必须应用于新设想的多器官范德比尔特移植模型,其独特的维度是在整个器官范围内进行,而不仅仅是心脏。
Norman Shumway 博士于 1949 年在范德比尔特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84 年在一次非正式聚会上 …[+]
医学博士比尔·弗里斯特
在范德比尔特新成立的移植中心,麻醉师、外科医生、精神病学家、护士、社会工作者、康复和物理治疗专家、临床科学家、伦理学家和传染病专家都将在一个地点相互交流,肩并肩,所有激光聚焦于患者。 许多医学、外科和研究学科在一个中心内自然、自由流动的交流将带来有待探索的新想法。 也许,我们在 1980 年代沉思,有一天我们甚至会在单肺移植方面取得成功,而在那些年里,单肺移植是出了名的不成功。
只有一个机构,匹兹堡大学,在著名的肝移植外科医生 Thomas Starzl 博士的领导下尝试过任何类似的事情。 但在那里,移植被按器官类型隔离到不同的项目中,没有地理上的共处。 在全国其他现有项目中,移植是围绕单个器官进行的,大多数都是围绕着一位知名外科医生进行的。 如此强调单个外科医生——或单个器官——通常会导致无法持续数十年的项目。 我们的目标是为一个能世代繁衍的项目奠定基础。
搬到范德比尔特:让梦想成真
回到斯坦福大学,同时还在完成我的奖学金,我正式制定了计划。 我整理了一份 45 页的商业、研究和临床提案,详细概述了新中心将如何取得成功,即使在心脏移植的第三方报销不存在的时候也是如此。 财务障碍是巨大的。
我接受了这个职位,并于 1985 年来到范德比尔特。
我们召集了设想中的多学科移植团队,共同制定了一个目标明确的使命,我们都围绕着这个使命在文化上保持一致:“通过教育、研究和临床方面的创新、多专业项目推进移植的医学和科学方面实践。”
我们组建的团队共同致力于将范德比尔特确立为全国移植领域的领导者——我们将通过包括和掌握整个护理范围来实现这一目标,从移植前的慢性护理,到外科手术,再到患者的长期护理和家庭移植后。 这比今天意识到“护理片段”对基于价值的护理的重要性早了几十年。 这不仅仅是“手术结果”。 在移植手术之前、期间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对我们的患者及其家人来说都是最好的。
幸运的是,范德比尔特有一些丰富的移植经验。 过去十年,Drs。 基思·约翰逊和鲍勃·里奇 一起在范德比尔特的纳什维尔建立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肾脏移植项目。 但宏伟的梦想远远超出了肾脏:我们将增加心脏,然后是肝脏、胰腺、骨髓、肺,以及心肺联合移植。 我们将招募一名具有专门移植知识的专门传染病专家,以在所有器官之间共享。 我们将聘请一名当时闻所未闻的全职移植伦理学家,帮助我们在这个移植需求旺盛但供体器官供应稀缺的新世界中做出生死攸关的艰难决定。 谁会得到稀缺的器官,谁会等待而死? 快速推进的科学程序在引入社会从未考虑过的新健康公平问题之前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在一开始就将考虑这些伦理问题的框架构建到中心中。
Bill Frist 博士和田纳西州 Donor Services 的器官采购专家 Doug Martin 关于“捐赠者 …[+]
约翰豪瑟/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中心
对于移植而言,准确且易于获取的数据对于成功比任何其他医学领域都更为重要。 我们需要实时的临床和财务数据,这样我们才能巧妙而安全地推进这个不断变化的新领域,而不仅仅是让它发展。 从第一天起,我们中心就开始衡量一切:成本、流程、质量措施、结果和功能结果。
移植成为最受监管的医学领域。 联邦政府首次明智地要求提供这些数据,不仅用于政府资助的程序,而且用于所有移植手术。 移植部门被视为公共产品。 在移植领域,我们在报告和衡量临床结果方面领先于其他医学专业多年。
过去的教训:创新的关键作用
当我们在 1980 世纪 XNUMX 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的旅程时,心脏移植还处于起步阶段。 每向前迈出成功的一步都会带来新的问题、新的挑战,这需要新的解决方案。 我们知道,创新和持续的再发明必须融入我们的文化。 因此,我们建立了一个团队,热衷于持续解决即将发生的问题。
我在波士顿接受外科培训时的一次经历告诉我,阻止创新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1980 年,作为麻省总医院 (MGH) 的心脏外科住院医师,该医院的董事会戏剧性地无限期暂停心脏移植。 这个令人惊讶的公告,其基本原理在著名的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引用了成本和功利主义哲学——他们写道,关键问题是“什么选择可以为最多的人带来最大的好处。”
我惊呆了——也深感失望。 我强烈认为受托人的政策决定,无论其用意如何,基于当时的科学,都是短视和误导的。 三十年前率先开展肾移植的医院怎么能禁止一项有前途的心脏手术,最终可以挽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医院领导层没有利用他们的众多资源来开创这种快速发展的新程序,而是突然关闭了可以改善患者护理的临床创新和研究的大门。 对临床创新的禁令扩大到波士顿的其他哈佛医院。
不可否认,由于我对心肺移植的未来充满信心,我离开了 MGH 和波士顿,加入了斯坦福大学的 Shumway,后者致力于强大的临床研究和创新。 在禁令最终解除后,波士顿花了数年时间才赶上其他中心。 对创新说“不”是要付出代价的。
范德比尔特心肺移植接受者聚会,1991 年。整体患者文化和 …[+]
医学博士比尔·弗里斯特
对创新和公平的制度承诺
从一开始,在范德比尔特,我们就把健康公平放在首位。 我们相信,这些挽救生命的创新不仅应该提供给少数愿意为一颗新心脏自掏腰包支付六位数的人。 范德比尔特大学的领导层,特别是董事会,支持我们向最需要帮助的患者敞开大门,而不仅仅是那些有能力支付费用的患者。 当然,最终我们的中心需要自己支付费用。 但在 1980 世纪 XNUMX 年代初期,保险公司还没有开始承保移植手术,范德比尔特承担了最初的患者费用。 这种明智的初始投资使我们能够尽早建立患者数量、积累数据并发展专业知识,以通过全面衡量的结果证明心脏移植对患者、社区乃至国家的巨大价值。
在我们开始成为霍尼韦尔和 Blue Cross 等公司的国家“卓越中心”几年后获得指定,然后是医疗保险,使我们能够为更广泛的商业保险和医疗补助报销提出令人信服的、基于证据的案例,从而增加了所有患者的可及性。 对创新和健康公平的投资为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我们文化和使命的基石。
积极参与公共政策
心脏移植依赖于供体器官的有限供应,这受到严格监管以确保安全和公平。 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大部分进步将取决于在州和国家层面制定和实施的公共政策。 尽管我们接受的是医疗队训练,但我们明白积极参与公共政策对我们来说势在必行。
执行范德比尔特首例心脏移植手术的 Walter Merrill 博士和参议员 Bill Frist …[+]
医学博士比尔·弗里斯特
我们中心的领导层支持并参与了政府授权的器官共享联合网络 (UNOS) 的早期发展,以确保所有美国人都能公平公正地获得这些新的挽救生命的程序。 有趣的历史记录是,1980 年代中期 UNOS 的原始模型是从先前存在的 东南器官获取基金会,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基思约翰逊和其他人积极参与并发挥了领导作用。
在州一级,当田纳西州在 1990 年取消州驾照背面的器官捐献卡时,我们中心发起并领导了全州范围内的基层运动,名为“为您的驾照赋予生命”。 两年后,捐赠卡被归还给过去 30 年来一直保留的许可证。
今天:世界上最繁忙的心脏移植中心
范德比尔特移植中心总共进行了 12,300 多例成人和儿童移植手术。 这是 目前正在表演 心脏移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都多。 对于所有移植,它是 第五 在国内。 它是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指定的为我们国家的退伍军人提供心脏和肝脏移植的少数几个移植项目之一。
该中心在其存在的第一个十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它建立在梦想之上——以及对科学、数据、创新和以患者为中心的文化和承诺。 随后的两个十年,其故事将由其他人讲述,见证了巨大的增长:
· 心脏:1989 年多器官中心成立的第一年(范德比尔特大学首次心脏移植手术五年后),我们进行了 28 例心脏移植手术,在全国名列前茅。 三十二年后的 2022 年,该中心创造了一项记录 141 次心脏移植,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中心(亚洲不报告数据。)。 这一里程碑是在 Ashish Shah 博士和 Kelly Schlendorf 博士的领导下实现的。 范德比尔特大学已经进行了超过 1,749 例心脏移植手术。
· 肾脏:范德比尔特大学已经进行了超过 7,100 例肾脏、胰肾同步移植和胰腺移植。 1989年完成肾移植89例; 这个数字增加了两倍多 315 通过2021。
Pam Everett-Smith,博士。 Frist and Merrill 移植于 1990 年,是存活时间最长的 …[+]
约翰罗素/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中心
· 肺:1990 年,我们启动了单肺移植计划,在作者和肺科医生 Jim Loyd 的领导下,第一年进行了五次移植。 2021年中心进行 54 次肺移植. 在该计划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已经进行了 700 多次肺移植和心肺联合移植。
帕梅拉·埃弗雷特-史密斯,我们中心 1990 年的第四位肺移植患者,是美国已知存活时间最长的单肺移植患者。 32 年前,Walter Merrill 医生和作者 (Frist) 为她进行了移植手术。 在 2021 年的一篇文章中 VUMC 记者, 帕梅拉分享说,“我现在 56 岁了,我认为我不会看到 30,更不用说 56 岁了。我只是感谢上帝给我的每一天。”
· 肝脏:1990 年,现为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中心副首席执行官兼首席卫生系统官的 Wright Pinson 博士受聘开始肝移植计划。 2021年中心进行 123肝脏 移植。 自 Pinson 博士发起该计划以来,已经进行了 2,700 多例肝脏移植手术。 Pinson 博士于 1993 年接替作者担任移植中心主任,并一直担任该职位至 2011 年。
几十年来范德比尔特移植中心的领导层从左到右:Seth Karp 博士,现任 …[+]
比尔·弗里斯特,医学博士,2022 年
范德比尔特大学还在扩大捐献者方面领先全国,率先使用暴露于丙型肝炎的捐献者移植未感染的接受者(然后在移植后进行治疗)和 体外 灌注系统,通过使用机器连续将血液泵入器官而不是在移植前将其储存在冰上,从而提高器官质量并延长手术时间窗口。
这是第一个十年的故事,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非凡的增长轨迹得以持续。 范德比尔特移植中心成立 30 多年后,继续改变着无数人的生活,超越了我们最早的梦想。 我们感谢许多为实现这一梦想而努力的医生和工作人员。 并特别感谢委托我们照顾他们的患者和家属。
资料来源:https://www.forbes.com/sites/billfrist/2023/02/06/how-the-busiest-heart-transplant-center-in-the-world-got-its-start–an-inside-第一个十年的故事/